很多年前有部电视剧,里面一位市长父亲在跟儿子传授“家学”时讲到了“含权量公式”的概念:Q=(S+C)/Z.
这里面Q即职务含权量;S为实际权力支配力,包括人事任免权、行政审批权、执法裁量权等;C为财政支配力,包括预算编制权、资金拨付权、项目投资权等;Z表示职级。
根据这套理论,剧中的官迷父亲认为“(同级别时)块块上的官比条条上的官含权量高得多”,劝儿子要多到“块块上”发展,走地方实权派道路。
原剧播出于2005年,如今回头看,当时确实是地方官员权力的“黄金岁月”,然而随着大环境更新,这种“条条块块”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
以当下的形势看,越往“块块”上走,需要处理的各种事情越多,堪称“钱少事多责任重”,“条条”上反而轻松一些。
更具体一点解释,现阶段基层的权力被逐步上收,乡镇乃至县里面有油水、有实权的部门大都被垂直管理了,剩下的许多是吃力不讨好的业务。
早些年间乡镇/街道主官宛如“十里侯”,拥有各种权力,而现在国土、财政、派出所、供电、工商等均为垂管部门,镇里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县里协调,以及处理农业、林业、防洪防灾、信访稳定等老大难问题——都是经常被问责的领域。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县、市或央企子公司、银行支行等单位,即越往下权力越小、资源越少、工作难度越大。
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开始放弃所谓的“实权岗位”,宁愿到大衙门里做一个事务性、技术性官员。
2024年6月,一则“禹州市医保局局长遴选至省府办公厅担任一级主任科员”的消息引发舆论热议。
公开资料显示,1993年10月出生的任小龙是研究生学历,自2021年10月起担任禹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是许昌代管的县级市,总人口130万,城区常住人口47万,距离郑州约80公里。
在2023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中,河南共有7地入选,禹州市排名第4,因辖区内人口众多、经济实力不俗,禹州市委书记有时还会由许昌市委常委兼任。
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百强县局长到省里去做个负责公文办理的事务性科员,似乎完全违背了“含权量公式”的理论。
与早些年间工作调动导致拖家带口的情况不同,随着交通日益便利,体制内的朋友往往倾向于将家庭稳定在一座中心城市,自己进行频繁通勤。
比如从市里调到县里任职的领导,他们的家庭一般会安在市里,爱人在市直单位或市里的科教文卫单位做个闲差,孩子也在市里上学。
同样,县里的领导、公务员到乡镇任职,家庭通常也安在县里,每天坐班车或开车通勤。
对于许多刚刚结婚生子的年轻人来说,工作调动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和家人团聚,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一种从家庭、个人生活角度出发的选择,并非像老一辈那样只考虑工作和“职务含权量”。
换言之,90后、00后的权力欲望其实没那么强,公务员在他们心中只是一份工作,这属于观念上的改变。
高压反腐形势下,体制内朋友越来越重视清清白白的工资性收入,权力带来的“灰色收入”需要打很深的折扣,甚至完全不予考虑。
而公务员的待遇情况通常是“省会/计划单列市≥省直>其他地市>县市”,面对当下基层“三保”压力较大的情况,往高处走、往富裕城市走成为很多体制内朋友的共识。
与上级单位相比,基层官员往往更早面临晋升天花板限制。
为了解决台阶少的矛盾,基层诞生了很多“隐性台阶”,比如同样一个副科级,镇人大副主席、副镇长、党委委员、副书记等,会形成层次分明的晋升路径。
当从科员晋升副科、正科时,市里、省里的公务员一般差别不大,但县里就不行。
再往上走,当从正科晋升副处时,副省级城市和省直单位的优势迅速凸显,普通地市则遭遇僧多粥少的困境。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副处在禹州市就是副市长,以当事人的履历,几乎不可能从医疗保障局局长一步提副市长,必然要再经过乡镇党委书记或其他多个岗位的历练。
然而放到省府办公厅,一级主任科员到副处只是一步台阶,跨越起来相对简单。
县城是一种圈子文化,因为地方太小,所以各种裙带关系就更加盘根错节——屋檐滴水代接代。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避籍”一说,即为了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规定不得在本省为官。
那这样是不是这样就能解决地方裙带关系滋生的问题呢?
很难,因为任何规定都只能针对主官,往下的副县长、局长和镇党委书记等并未有类似要求,或者说根本无法做同样的规定。
毕竟越接近基层,工作内容就越具体和微操,越需要接地气、熟悉当地实际情况的干部。
前面提到了,县城官员的晋升天花板非常有限,除了县委书记、县长和个别垂管单位领导能够异地升迁外,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地完成了几十年的仕途——科长、副镇长、副局长、镇长、镇党委书记、局长……
考虑到县城的圈子本身不大,本地干部又长期生活工作在一县,一种基于亲属、同学、同僚等人情元素的利益关系便自然而然形成。
套用一句耿彦波的话,他们才是这座县城的“主人”,其他那些调来调去的干部不过是“客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对于那些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如果没有足够外力支持以及长期扎根一地的决心,想要打开局面十分困难,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会让人感到心力交瘁。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大多数工作都可以按部就班走程序推动,没必要事事都“刷脸”“找关系”“卖人情”。
经过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大学阶段后,许多大学生已经习惯了城市里人际交往的方式,假如突然将他们置于小地方“圈子文化”里,会产生明显的水土不服,有时还不如一些本地二三流院校学生吃得开。
以祁同伟为例,他汉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岩台山区一个乡镇司法所工作,期间萌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和调动意愿,为最终黑化埋下伏笔。
但反过来思考,如果把一位当地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安排进来,说不定更珍惜这个岗位,会踏踏实实干上几十年。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对于体制内工作的认识正在经历一种返璞归真的转变。
在1990年代到2000年初,“当官”几乎天然意味着财富、资源与社会地位,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权力崇拜。
但在反腐高压和市场经济多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公务员本质上也是一份职业,而非特权身份。
权力的“附加财富”属性正不断下降,对应上升的是责任与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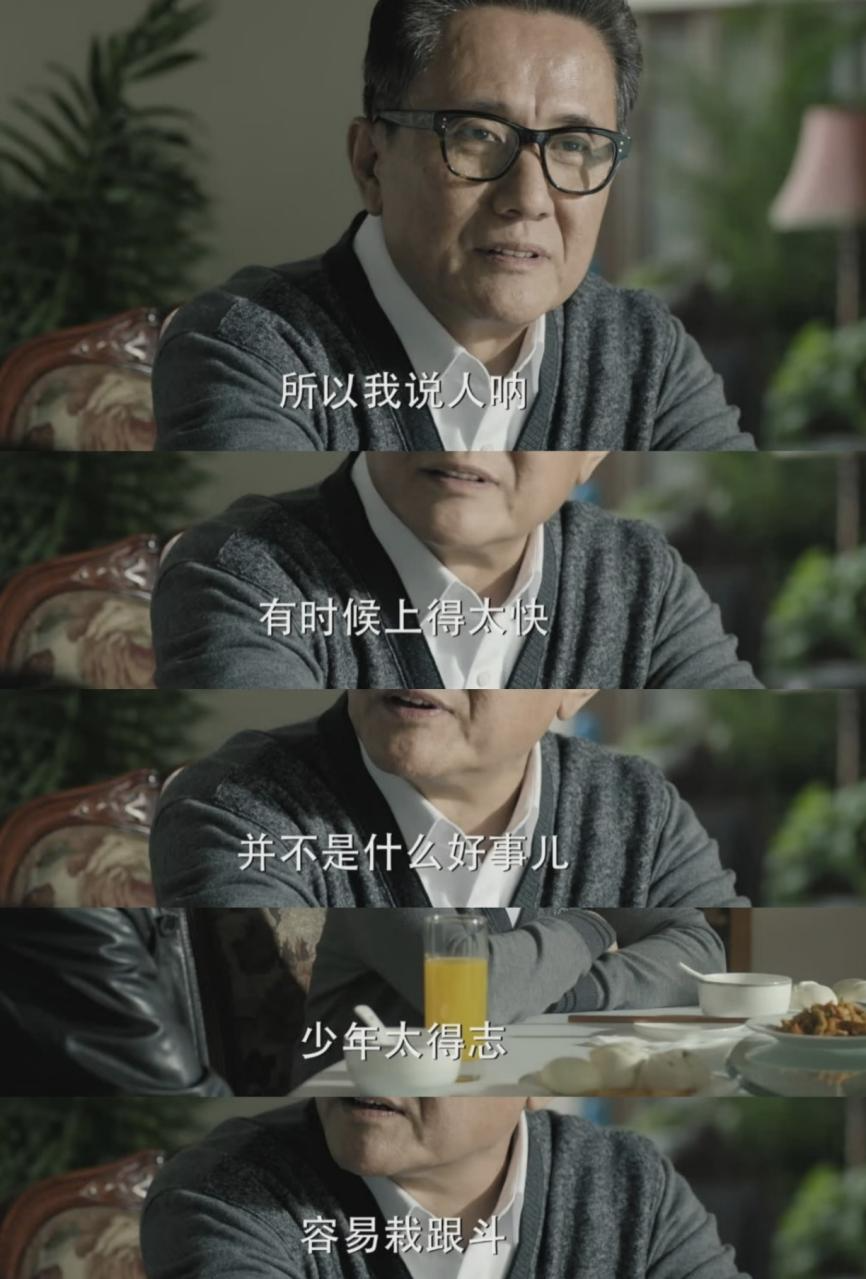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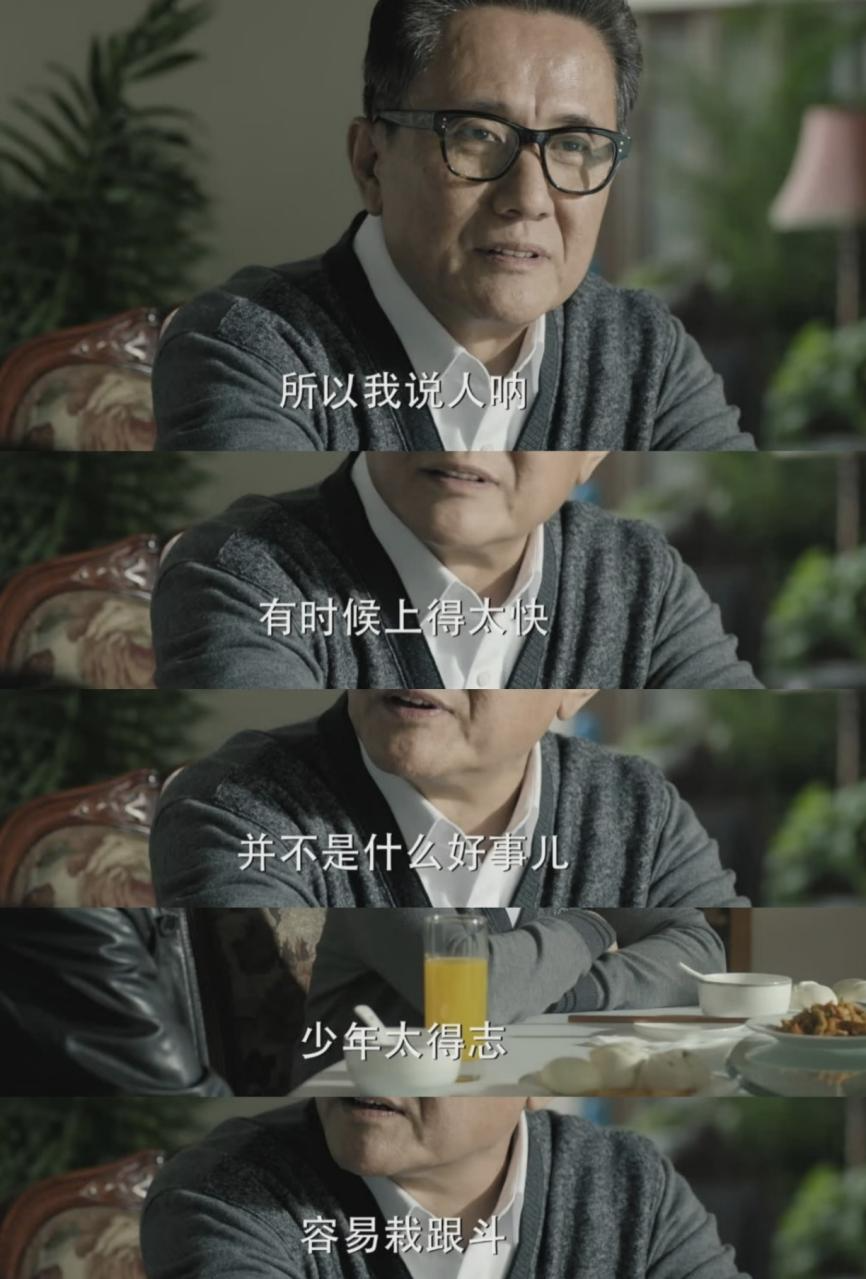

发表回复